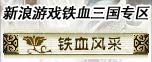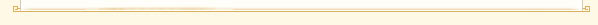|
(一)前言
蜀相治国为民,或是篡位争权,与其争论两种评价,不如认清生平史实。
历史事件与人物评价,必有其前因与后果,时间顺序与来龙去脉。因此若要高谈“竖立神像”云云,最好把诸元详列,举凡何人立神、何时所立、何地竖神、历时多久以及众人赞成与反对等等,才能彻底明了。否则空谈不知何人所立何神,以及所产生的何时褒贬,宛如雾中看花,愈看愈花,得出来的结果当然是天马行空,不切边际。既云孔明篡位,最好把孔明何时罢免皇帝、登基称帝的时间找出来;强调孔明夺权,当然应该也能指出孔明夺走何人之权,否则难称孔明“篡位夺权”。
依“疑罪从无”原则,没有证据就是不支持犯行。
传统虽有儒教之名,却无宗教之实,高举神坛崇拜,反缺史实褒贬。因为儒家本非宗教,若抹黑儒教当成邪教,历代大儒所著古典文献不就全变成宗教书籍。仔细看清是谁“竖立起一座神像”,然后谁又“付出代价”,这个代价还要对得起“整个民族对历史的误会”,误会在何处等等。
评价基于事实,没有事实支持的评价,宛如无根浮萍,任人摆布皆可,与其争辩,不如认实。孔明生平从出仕、治国、到用兵,正是一生三大部曲。
一定讲得清楚,才能说得明白。
(二)出仕
“自比管乐”与“不求闻达”非为心口不一的对立词。
因为前者乃为志向眼光,后者则为现况事实,一个是所思内心,一个是身处环境,身心当然不同。“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所指孔明自认才学比得上管仲、乐毅,或是说孔明向管仲、乐毅学习等,本是向上看齐的心态。再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所述则为孔明布衣躬耕,并无汲汲向诸侯求官有所闻达。
两句若要心口不一,不是说孔明“心向管乐之志”而“躬耕务农之实”不对,就是孔明“务农生活”而“心怀大志”不实。仍细思考,怀才未遇之人不逢富贵,并不意外;或是身处箪瓢屡空,却心有冲霄凌云之志,司空见惯。除非怀志者不能躬耕务农、务农者不能妄想出仕,才有地主的儿子一定得当地主,贫农的儿子一定得当贫农的这种封建思想。
虽自比管乐而怀才未遇,故躬耕田亩;又因躬耕苟活,故不求闻达于诸侯。有大志之人,所以才不甘寂莫于农耕;一人农耕,收获有限,不如从事治国辅政,造福更多的人。
若是汲汲营营于名利,早在家乡转投陶谦或曹操,或于荆州投刘表,若无刘备三顾,孔明恐怕就得归隐终老。这正为孔明原本无人可依而不求闻达,淡泊名利之初;后逢刘备知遇之恩,因此鼎力相助。此时若反批孔明不肯改事孙权,就有点违反忠诚之忌。因为刘备三顾孔明在先,张昭替孙权拉拢孔明在后,若是孔明先归刘备不久就改节易主,另拜孙权为主,反倒有不忠之讥。而且孔明称孙权器度不大,也是颇有预知的道理,孙权能贤人而不能尽人,举凡周瑜、程普、鲁肃、吕蒙及陆逊皆然,这些江表诸公一生皆无法放开手脚,屡受节制或退用。要是孔明仕事江东,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还镇某地”、“留镇某城”或“还备某处”,寿命短一点的人,可能就未发挥长才郁郁而终;或者是像张昭这种重臣,“在里宅无事”而度过余生,寿命太长也无济于事。
“宁为鸡口,无为牛后”更是人往高处爬的理想,曹操不曾亲寻访才,孙权还派人录用孔明,只有刘备礼贤下士,因此面对盛情难却的要约,必有前途,正是从各种最有希望之中的最有利之抉择。曹操既不求人,孔明若投靠只是自行倒贴,但未必受欢迎;孙权用人只凭关系或介绍,孔明若不想依靠门路,毋须同流合污;刘备三顾茅芦,诚心用人,将来必有可为。孔明出仕,并不违反当初“不求闻达”的初衷,有大志之人,岂有一辈子默默无闻的道理。况且刘备的求才诚意感动孔明,得名主而共成大事,同秉复兴汉室大业,故“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因此孔明虽曾一度“不求闻达”但基于传统“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实为执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怀才不遇并非“心口不一”,“绕树三匝,无树可依”时不必勉强委曲求全,得逢名主是以己达而达人。
再来是向刘备及刘禅夺权篡位之疑,但查刘备及刘禅未对孔明传位,孔明亦未称帝,因此篡位之诬,着无庸议。又如夺权法正、许靖、孙干、简雍、廖立、彭羡及李严等人之职,更不消多云,孔明丞相之位不由继位而来,前述蜀臣存亡与否,孔明仍能以相位领导百官。
(三)严法治蜀
法家原出诸儒,著名的李斯及韩非皆出身于儒家荀子之门,在汉儒“以经解法”及“以经代法”的形态,儒经在秦汉本来就是执行法律的精神。因此以儒执法才符合传统,这里的“经”指儒家经书,而非法律典籍。
若把近代资本主义之法律,即欧陆文艺复兴以后的“法治”当成是唯一法律基础,不但错失自罗马法以来的宗教神权代理及立宪国家化,也误解海洋法系的不成文法,以今非古并不宜。当然对先秦两汉以来,断讼治吏却引经据典的情况,对所谓“法治”更是莫大的讽刺。儒法讲究的“法先王”与“法后王”差别很大,若与“法老王”相比,差别更大,这正是误解而失其意,“差以毫厘,失之千里”的道理。虽以陪审团的人为合议方式判法,但不会有人说不列颠海洋帝国的法律就是人治或非法治,因为法律的精神基于人为而实现伟大,自古皆然。这也是以人实践法治的精神,孔明治蜀正属此类广披法律精神。
益州五子共造《蜀科》,即孔明、法正、刘巴、李严及伊籍五人合订法律,是不是孔明专制独断,已经一目了然。又如《五惧》、《六恐》、《七戒》、《八务》等法律,均以明令成文而约束官吏,而不是凭一己的喜恶而陟罚臧否。要人死,就处以犯兽绞死;要人活,虽杀人无罪。或是不教而杀、不戒视成等虐暴。这才是典型的人治,而且苛政无法。
豪强没有特别于平民,因此没有法律豁免。门阀世族不过是比小康之家多了几口人、家产多了几块田,没有理由被视为精英而不比照平民纳税服役。原先刘璋统治下益州豪强(包括江东士族门阀也一样),“思为乱者,十户而八。”这当然要下猛药以行公平,“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故以“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这正是法律上的公开、公平及公正。“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不见于当时的《律》《科》,但却有实际法治的效果,如果这就叫“人治”,为何江东“王与马,共天下”的人治,却没有造成“法治”呢?东吴孙权严刑之酷,可谓厉行峻法苛刑,但东吴反有暴政之称,同样是人治法律,为何蜀汉美其名为法治,而东吴恶其实为暴政呢?曹魏历代修订法律,同样落实执法,曹魏亦有法治之名。魏蜀吴三国同为以人治国,为何魏蜀同享法治之名,吴却有暴政之恶呢?区别不在以人而为,而在法治之精神。
因为“以境劝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此类见于儒经之民本,正是造就法治的基。养民牧民,孳生自强不息,胜过掠民捕捉“以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因为竭泽而渔无异于杀鸡取卵,法治之目的在造福人民,而非逼迫人民以实现严刑峻法,这才是严打的精神,目的证明手段正确,而非削足适履本末倒置,法治为民而非逼民守法。
李严不被孔明在《出师表》提起,这很正常,如果有读过《出师表》就知道,孔明北伐出师,上表刘禅“亲贤臣而远小人”,因此希望刘禅亲信“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这些“贞良死节之臣”,或是将军向宠“晓畅军事”等,没有必要提起远镇永安的李严,难道刘禅有事还得亲自到永安向李严咨询吗?除非把李严从永安调回成都,刘禅才方便宣召李严进宫,这样孔明就可在《出师表》记上一笔,让刘禅接见李严,不过这样又会有人说是剥夺李严兵权。
从“部分如流、趋舍罔置,正方性也”到“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事。”两种评价,真正反复的人是李严本人,而非所称道的孔明前后言辞不一。道理很简单,李严没犯错时,当然获得佳评,李严犯罪时,当然饱受批评,这不是评价前恭后倨而言辞不一,而是当事人的行为判若两人,从无辜到犯罪。
从李严、廖立及彭羡等人,犯罪被罚,可说罪有应得。毁谤先帝、阴谋造反、扣粮谎报,并非小罪:按《汉律》毁先帝属“不道”,判罪最重可夷三族;叛逆未遂及造反,亦是诛族连坐之重罪;担误运粮假报军情,属汉律“不敬”,判罪最重可夷三族。孔明未从重量刑,已开仁慈之门。廖立若为孔明政敌,骂骂孔明也就算了,非议到刘备头上,当然找死;彭羡动不动就想造反,古代叛变可是抄灭族的重罪,忠臣能不慎言吗?李严误粮不肯承认,还上旨欺君,下场不死也得被黜。此三人若真犯行无辜,也太不识轻重,要是落在江东校事(即现今之特务)吕壹的手上,早就三家血腥。而且依法判刑,罪有应得。
孔明说要严法,实际用法重刑,表里一致。
(四)出师陈表
孔明用兵南征北伐洋洋洒洒,这里仅就北伐上表讨论。
统计字数,不过就是文字出现的次数,不代表全篇意旨。若是“先帝”出现十三次,就是全表具有“老子”的高姿态;那孔明称“臣”出现十五次,不就全表显示“臣属”的卑屈?“宜”与“不宜”才各出现三次,就变成“爸爸教训儿子”,而“陛下”出现七次,是不是又代表“君权至上”呢?
“先帝”十三次就叫多,称“臣”十五次不就更多;“宜”与“不宜”合计六次,还不如“陆下”出现七次。十三比十五多还是少?六比七多还是少?简单算术问题数不懂,若因此看成“咄咄怪事”而“终日书空”也不奇怪。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若批评成“霸道的言辞”,或称之“破坏朝廷正常礼仪和官场秩序”,以及“公私不分”等,把原本“执法公正”,把外朝及内朝的大臣公平对待,赏善罚恶,不宜偏私,不可使内外异法等,反变成无限上纲的无穷延伸。汉廷本为中央集权,而非诸番联邦或各国联盟,周室封建的“亲亲”,早被秦朝的“贤贤”取代,因此秦朝两汉的郡县天下,则是地方都得服从中央,而且同律同刑,若有不奉中央正朔,则视为叛逆。孔明建立法制,正是希望“大公无私”的法治精神得以飘扬。若是刘禅宫中不遵国法,若有藏私包庇,枉法贪渎等情事,也不应网开一面。
“亲贤臣、远小人”正是全表要旨,本来是很理直气壮的为臣表达忠君爱国之心,但若臆度成篡逆权臣安插亲信以控制皇帝,未免太以小人之心而度君子之腹。或者是借上表昭告群臣,孔明已经控制刘禅之类。事实上出师陈表,读表所见不过皇帝一人,又不是孔明传檄昭告众臣。
若是朝中尽是孔明人马,孔明又何需上表表态呢?若是朝中均无孔明人马,孔明上表也无济于事,因为蜀汉诸臣难以接受孔明上表,臣下向君主陈述意见的其中一种文体才叫表,孔明若有僭臣之心,谁敢接受孔明陈表?孔明与李严不过互书,除了皇帝外,还有谁能让丞相孔明陈表呢?既然群臣当时看不到孔明陈表,诸如此类臆度安插亲信控制皇帝的表态,想象力极为丰富。
再说孔明此次出师,军屯汉中后,再也没有回来,命丧五丈原,连尸体都没运回成都。
从“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把孔明心怀刘备感遇之恩,以复兴汉室为己任,不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篇出师上表要刘禅“亲贤臣、远小人”,孔明以相父今后离开,望君珍重的感情,交代刘禅好自为之,本来字义如此简单。最后追述三顾殊遇,表明北伐本意,反复叮咛刘备察纳雅言,访求治道,既有君臣之义,亦父子之情。因为刘备临终曾托孤孔明,使刘禅视孔明为相父,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把临终托孤看成骂街之想当老子的臭咒,又是以小人之心而忘却史实,刘备临终托孤遗嘱孔明。
若反认为其中必有阴谋,不妨就针对史实与言论作一比较:
一、孔明上表说要北伐;实际上也真去北伐,一共有六次大规模用兵。
二、孔明建立法治,希望刘禅“亲贤臣,而远小人”;刘禅后来先用蒋琬、后用费袆,几乎悉数任用孔明的用人安排。
三、若反说孔明安排亲信,控制刘禅;刘禅仍在成都称帝,倒低有无被挟胁,又被谁挟天子以诸侯,耐人寻味。
四、再反说孔明陈表昭告诸臣,文宣掌控;此时李严人尚在永安,彭羡已被诛杀,廖立已被废为平民而徙放汶山郡,均无机会见表,还有何人反对孔明而有机会接受孔明陈表?
孔明出师陈表,故长征而去,名符其实;又不是《受禅书》,强逼刘禅下台,或是叫刘禅出师打仗送死,临前出师上表,难道刘禅就因此被此一表所控制?孔明上《出师表》后出发长征,“心口合一”相符,又不是上表拒不出发。
事实向来胜于雄辩,没有根据的狡辩,抵不过简单的事实。
(五)检讨后语
还是看不出来孔明何时被拱上神坛,或立为神像,倒底是孔明生前被神化,还是孔明死后被神化,究竟是谁主导神化?有何任何政治利益或是对人民洗脑之类。因此倒底有没有人要出来“付出代价”,这也很纳闷,而且整个民族还要对历史造成误会等。用不确定的猜疑,凭籍不确定的事据,居然得出斩钉截铁确定的结果,这才奇怪。
若说孔明的心口不一,从出仕、法治到出师上表,就会被拱上神坛,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或是敢不敢“正视历史”之类。因为孔明就算“心口不一”,这与“登上神坛”,一点也没关系:任何人不会因为掩盖罪恶,而被封神;不过是就仕、治国、出征陈表的简单史实,也难以评价神化。事实只有一种,评价却纷杂多变,而且远离事实的评价,必然不实。
务农而有大志,若当真为“心口不一”,可能是暗示种田的人一辈子都得种田,居然妄想飞黄腾达,好像人不能往高处爬,否则就是“心口不一”。乱世本用重典,因此宣传法治,实际厉行治国,这种言行相符之事实,若此行反称“心口不一”,不知是否暗指实际施法不严,就算从李严、廖立、彭羡被罚,更可看出贯彻严法,难道被杀、被贬、被下放还不够严法吗?法既严,刑必行,表里合一。至于《出师表》有无心口不一,用字数的统计只不过以偏盖全,文章不仅看字,更要看句成文。“亲贤臣、远小人”更是一般性原则,孔明劝谏刘禅任用贤臣,而实际上刘禅用不用贤臣则在于刘禅,就算刘禅大用小人,有违孔明《出师表》的初衷,这也不能怪孔明“心口不一”,盖国之用人,定夺在君,为臣辅佐,仅能建议。皇帝用人根本毋须陈报丞相核准,因此刘禅亲不亲贤臣,近不近小人,完全不是远离皇宫的丞相所能控制。
孔明生前的最高职称是“丞相”,不是“神”;孔明死后有没有登基“神坛”,或是摇身变“神”,“或是替天行道,代替月亮惩罚你之类...”,此点含糊;但是批斗孔明甚至要“拉下神坛”,最好先把孔明神化的过程交待清楚,否则都是捕风捉影,一味疑鬼疑神。孔明生平无法自行封神,孔明也无控制后人造神,因此神化孔明与否,与孔明本人无关。
因为“心口不一”不是神化的必要条件,而且孔明非以出仕与否、严法松法及出师上表等事就能升格为神。如果诬指“心口不一”与“拉下神坛”之间没有关系,在“心口不一”打转,对“神化”与否并无影响。“心口不一”事宜都搞不清楚,当然“拉下神坛”之类也就说不明白。
自己竖立草人,再对草人猛批,不如当初不设草人即可,狂揍草人只不过是推翻当初所立草人不正确。就拿盛传“曹操是女人”来批“性格猜疑”一样:前提为人不论男女,早已与性格无关,女人固然善疑多忌,男人常猜亦很平常;至于曹操男女之辨,更与性格无关,因为是男或女都不能影响性格猜不猜疑;最重要的是谣言没有根据,并无曹操属女的凭据,前提既错在先,推论又错在后,结论当然导错,错上加错只是错错错。
同一件事情,一百个人可以有一百种评价,与其周旋于各种评价之间,不如简单返扑归真,端视事实与评价的差距。各种谣言可以没有事实根据,但同一事实却可以产生各种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