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软件》:朋友 祝你愚人节快乐
发表于2010年《大众软件》4月中
策划 本刊编辑部
执笔 大豪斯领主
一个不值得庆祝的节日……
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荒地上
长出丁香,掺杂着
回忆与欲望,又有春雨
催促着愚钝的根芽。
——艾略特《荒原》
如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艾略特并不是通过抽签选中四月作为“最残忍的月份”的,四月之所以被诗人赋予这一称呼,很可能并不是因为春雨或丁香——在我们所熟知的十二个月份中,没有哪个能像四月一样拥有一个如此残忍的开端:四月一日,愚人节。
对于一些一年四季都在研究电击效果,以“孩子,你需要治疗”为口头禅,视游戏为死敌且缺乏幽默感的家伙而言,这个日子只意味着无尽的谎言、欺骗、放纵,道德的沦丧与出于纯粹恶意的嘲弄……但是,嘿,那样的家伙是没机会拿起这本杂志并看到这些内容的,如果幽默感缺乏到了那种程度,那么残忍的绝不会是四月,而是每个月。对于所有无需参与电击治疗的幸运者而言,我们可以为了四月的第一天而干杯庆祝:每年我们能体验到四月残忍的时间只有这一天。

这一天可能会从被拨快的钟表提前两小时响起的闹铃声开始——如果你碰巧需要上学,那么请不要对此感到恼火,应当为闹钟没有被拨慢两小时而感到庆幸才是……如果你遭遇到了这种事,那么上早自习时,课代表或学习委员很可能会“提醒”你忘了写某门课的作业,这时请不要表现出惊讶——在这个日子里,你可以不相信别人,但更重要的是你要更加相信自己。午饭时,你可能会在食堂里看到堆积如山的馒头,如果你没有被它们的外表欺骗并绝望地扭头泪奔出门,就会发现里面的馅要比包子还要厚道。如果哪位老师突然宣布“随堂考试”,那么你可以保持淡定——因为这节课很可能在一分钟后就会开始自习,但如果你的同桌告诉你今天提前放学的话,你就需要保持警惕了,如果他拿着一本《大众软件》4月中旬刊,指着专题中的一页宣布“你知道么?这个游戏要出了……”,那么你不如告诉他,呃,“你知道么?今天提前放学……”。嗯,如果他因此开始欢快地收拾起书包的话,你最好还是制止他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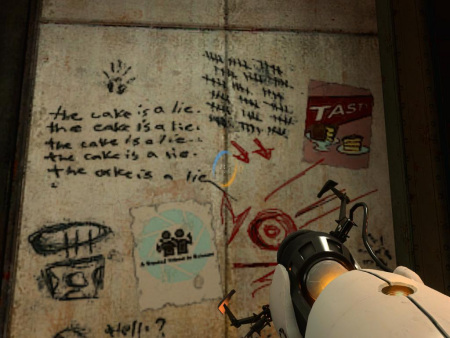
是的,这才是愚人节!
但是,等等……为什么这一天会是愚人节?
庆典?混沌?愚人船
在我们所知的诸多“节日”中,没有哪个像愚人节这样充满混沌的气息:节日往往有纪念或庆祝的功能,而这样的日子需要一个明确的对象或目的,但愚人节则完全不具备这些条件和特征,节日往往建立在一个具有凝重历史感的背景之上,与之相伴的习俗则是以传说或神话为基础——而这些在愚人节中也毫无影踪,我们甚至不能为愚人节的源头找到一个权威、确切的典故,究竟是什么未曾见于书面的规矩让人们在口口相传中形成了这一风俗?人们为什么要约定在4月1日彼此交流精心准备的谎言?为什么欺骗行为唯独在这一天可以不受谴责?
解读愚人节的关键在于追根溯源,在这个过程开始之前,我们有必要区分两个概念:“愚人节”这个称呼可能会造成一些误会,同一个词可能会被用于称呼两个不同的对象,“The Feast of Fools”(直译为“愚人的节庆”)和“April Fool’s Day”(直译为“四月愚人日”),后者才是我们在有生之年所面对的每个4月1日,而前者则是可上溯至中世纪的古老的狂欢庆典。
无论中世纪的欧洲给你留下的印象如何,对愚人的节庆的考察都可以为你翻开崭新的——且内容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一页,挪威卑尔根大学的英格维尔特?萨利特?吉尔胡斯教授在《宗教史中的笑》一书中曾对此进行过详尽的考证和描述,她将愚人的节庆归类为“在天主教领导的几个世纪中,欧洲泛滥成灾的‘笑文化’”之一,这一节庆的具体内容与教会在历史中的表现有着极大反差——几乎构成了完完全全的逆转,首先是等级森严的教会制度被完全颠覆,低等的神职人员和助理执事怀着最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一节庆中,在节庆期间,这些人穿着破破烂烂、或故意将衣服反过来穿,甚至穿着女性的服饰,在教堂中打闹玩耍,在闹市与街道中进行恶俗的表演,同样被颠覆的还有弥撒与圣餐礼,这些神职人员几乎篡改了仪式的全部内容,打破了所有的禁忌,甚至会发出如驴一般的嘶鸣,或者直接将驴子牵入教堂,对其高唱颂诗……关于这一节日最早的记载出现于11世纪末,时间跨度长达数个世纪的相关记载证明这一习俗曾在中世纪时期的天主教国家内盛行过几个世纪,尽管教会的权威神职人员一直对此持否定和批评意见,但一节庆却直到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之后才被移出“传统”之外。

这一节庆并非是为了纪念或是为了庆祝而展开,它的目的毫无遮掩地反映在其名字中:“愚人”,在那个尚能允许愚人的节庆盛行的时期,颇有创造力的下层神职人员曾是如此向教会的权威提交相关申请:这一节庆是由必要的,因为愚蠢是我们的第二天性,愚人应该可以自由地放任自己,至少一年一次。如果不是我们时不时地打开酒桶让发酵产生的气体释放到空气中去,酒桶就会爆炸……

如果对其嗤之以鼻,扔下一句“陋习”就置之不理,对于这些文化资源而言就实在构成了一种浪费,因为这些看似不可理喻或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对于学习历史、解读异国文明以及了解我们自己都会有所帮助:在压抑环境下寻求释放、对森严的等级制度的反抗,还有对“笑”的追求与向往……这些不但不是无法理解的,还是人性中共通的部分,正是愚人的节庆为这些易被封锁禁锢的欲求挖掘出了一条通道,对于满怀热情参与到该节庆中的人而言,其美好是毋庸置疑的,尽管这一美好建立于混沌之上——但又有谁规定过混沌与美好无关呢?

中世纪愚人的节庆并不是近现代4月1日愚人节的起源,但两者在精神上一脉相承:社会规则对人们言行的约束临时解除,短时间毫无顾忌的放纵得到允许,放纵言行所造成的后果可获宽容……但参与这一节日并不是无条件的,这个节日有着自己的规则——以“愚人”这个称呼为基础而建立的规则。
福柯的《疯癫与文明》的经典之处与重要性在这里已无需多言,之所以要特别提到这部著作,是因为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让读者得以借此进入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并由此认识“愚人”对该环境的价值和意义,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颇为值得琢磨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大多数情况下,整个欧洲并不刻意将“愚蠢”与“疯癫”区别开来,“愚人”几乎就是“疯子”的代名词,两个词所能起到的陈述作用、所表达的反感和谴责的对象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两者之间频繁出现的并列和替换似乎一直在暗示读者“愚人”与“疯子”的共同之处不可忽视:两者的区别很可能只是病理学所研究的课题,但并非从事医学研究和治疗工作的人无需做出这一区分。
愚人与疯子在什么意义上,有何种程度的相似呢?不一定需要锁定多个目标进行长时间观察,就算仅凭常识与想象,我们也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对正常的社会秩序而言,两者可能造成的破坏和构成的威胁是极为相似的。两者可能同样表现为判断能力的缺陷,并由此导致行为的异常——但因为这并非“故意而为”,正常的社会秩序有必要对其表现出宽容:对其行为后果不予追究,不强迫其按正常规则履行义务,换言之,就是解除社会规则对其言行的约束——因为他们无法被约束。

正是这些使得愚人的节庆——以及近现代的愚人节的出现和持续存在成为了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常的社会会对这些群体张开慈爱的怀抱:这个群体所能享受的最大限度的仁慈就是不被社会规则约束,而不被约束并不必然意味着自由,他们的命运可能会是长达终生的监禁和放逐。
这种奇异的“醉汉之舟”沿着平静的莱茵河和弗兰芒运河巡游……这种船载着那些神经错乱的乘客从一个城镇航行到另一个城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