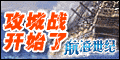丛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宽。
明朝晴更好,飞翠泼征鞍。
观此五言律诗,辞旨清丽,构意精巧,意气昂扬,反映出作者不凡的才情与文学造诣。叹赏之余,谁也难以想象,此诗的作者竞是一位明朝历史上令人谈之色变的“倭寇”。生活在杭州湾畔的海宁人采九德曾亲身经历过一场所谓“倭寇”劫掠,这一群“倭寇”不过四十余人,其中一位临走之时,诗兴大发,在影壁上题下了这篇诗文。采九德在所著《倭变事略》中照录此诗后,感慨系之:“观此四十余贼,亦有能题咏者,则倡乱者岂真倭党哉?”很显然,即使是日本国内的汉学方家恐怕也难以挥洒出如此高妙的诗文,况且这种日本高级文化人并不多见,因此,这篇诗文的作者定为中国饱读诗书又怀才不遇的文士。采九德的怀疑确为我们了解明代“倭寇”问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有明一代,甚嚣尘上的“倭患”问题让朝野上下伤透了脑筋,而所谓“倭寇”是否为纯粹的日本国人,颇难一概而论。
古代中国与日本的交往可谓源远流长,随着地理知识的丰富与航海技术的提高,彼此间的往来开始变得愈来愈便捷。秦汉时期,日本诸国前往中国一般循朝鲜半岛北上,路途相当遥远,“渡三海,历七国,凡一万二千里”。但从六朝以后,日本人到中国多从南道浮海而来。如北宋雍熙年间,一位日本僧人由海路到中国后,曾上表陈述其旅途:“望落日而西行,十万里之波涛难尽;顾信风而东别,数千重之山岳易过/信风的帮助可以使漫长的航路变得轻而易举。同时,从中国到日本,也相当便捷,他当时是从浙江台州离开的,“季夏解台州之缆,孟秋达本国之郊”。而日本群岛呈南北纵向分布,南部诸岛屿与中国闽。浙沿海地区的交通显然更是快捷。
日本至中国南路航线的开通,在中日交流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它为两国民间交往与海上贸易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当然,这种民间的交往受到相当严重的制约。应当指出的是,海上航路的便利也给中央王朝的海防建设带来了新的考验。长期以来,日本群岛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南部诸岛的武士与商人开始进入中国沿海,进行走私及烧杀抢掠等海盗活动。日本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称为“倭国”,因而中国朝野便将入侵骚扰沿海的日本海盗称为“倭寇”。中国海岸线漫长,沿海抗拒官府的绿林人士也大多以海上诸岛为根据地,内外势力极易联手,共同向中央王朝的边区发动剽掠。这种严重的态势在明朝初年就已显露无遗。
元朝未年,江苏泰州人张士诚。浙江台州人方国珍分别在当地起兵反元。张士诚占领高邮等地后,控制了作为元朝南北交通枢纽的大运河。同时,方国珍起义军夺取了元朝运粮船只,以浙江沿海为根据地,阻断了元朝漕粮北运的海路。这两支义军中有不少是熟悉水路、精于海战的渔家子弟。元朝政府为恢复东南潜运与海运之路,用高官厚禄诱降张士诚与方国珍,但他们往往屡降屡叛,依!日各自占据着自己原有的地盘。如张士诚全盛之时的辖地就“南抵绍兴,北越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颖、壕。泅,东薄海,二二千余里”。东南沿海重镇如宁波。绍兴。杭州。苏州等地,均在张士诚的势力范围内。方国珍的地盘,则主要限于浙江庆元。台州、温州三路。后来,在朱元漳军队的进攻下,张。方两个割据政权先后败亡,但其残部大多逃亡海上,成为出没无常的海盗。更为严重的是,这些“负固海岛”。行劫江湖的中国海盗与日本倭寇勾结起来,并为之向导,联合向明朝沿海地区频频进犯,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海患”。他们所到之处,焚烧民舍,掳掠财物,北起辽东半岛,山东,南抵福建。浙江。广东,“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
明朝初年“倭患”的出现还有一些客观背景。14世纪初,日本进入了南北朝对峙时期,大大小小的诸侯各据一方,力争夺土地与人口互相攻伐,战乱迭起。在争战中失利的封建主及其武土们组织起来,到中国沿海进行武装走私,一有时机便大肆杀掠。元末明初中国改朝换代的混乱更给了他们可乘之机,因此,在从辽东半岛到广东、海南数千里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在在出没”。可见,当时“海患”的性质较为单纯,主要有两股势力涉足其中,一是中国方面与官府对抗的海上绿林人士,即“岛寇”;一是日本方面的武装走私者。
为解决这种海盗性质的“倭患”问题,朱元漳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他在以重兵武力镇压的同时,派遣使者照会日本国王敦促其制止国人的侵扰行径。但日本执政者答辞简漫,毫无诚意,这使朱元漳十分不满。不过,鉴于元朝进攻日本严重受挫的历史教训,明太祖采取了克制与忍让的态度,力求从本朝内部解决问题。为断绝中外海盗的耳目与内应,他下令禁止滨海居民私自出海,并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大量招纳原张土诚。方国珍部下军士及濒海的船户。岛人、渔丁为兵,自淮。浙至闽。广,共计十余万人。这可以说是明朝实行海禁政策之始。这种政策虽然断绝了无数渔民的生活来源,但由于大量渔民被籍入伍,事实上由国家供养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由海禁造成的严重矛盾。
洪武十三年(138o年),左丞相胡惟庸谋反事发,据供称,日本官府与之有勾结。日本贡使伏兵于贡船之中,并将火药兵器藏于人贡的巨烛之中,等进宫朝见时,内外一齐动手。事情败露后,朱元漳无比气愤,毅然决然地断绝了与日本官方的关系,开始着手在沿海建设大规模的防务工事。洪武十七年(1384年),汤和等筑山东。江南。江北,浙东、浙西海上59城,以备倭为名,设置行都司。二十年(1387年),周德兴往福建福、兴。漳。泉四郡,筑海上16城,籍民为兵,以防倭寇。这种海防建设称得上是朱元漳的创举,对于保障中央王朝海疆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明朝政府还增置沿海卫所,添造多橹快船。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从辽东至广东沿海共有五十多卫,拥有士兵二十余万,而且防御设施相当完备。如每卫有5个千户所,备有战船5O,每船旗军50名。也正是由于拥有了强大的海防力量,才使洪武一朝的“海患”得到有效遏制,未酿成大患。
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棣命太监郑和等率舟师3万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航海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为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显示“天朝大国”的“物产丰饶”与“慷慨大度”,郑和携带大量中国珍奇特产,遍行赏赐。海上诸国对中国的珍宝财物极为艳羡,因而千方百计向明朝官府靠拢。日本国首先遣使致意,表示愿意“归附”,并提出“人贡”的要求。当然,这种“归附”与“人贡”只不过是一种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中国与日本两国间有某种归属关系。在中国封建时代,外国人到中国的所谓“人贡”,其实是一种不平等的经济交换关系,即“贡”少“赏”多。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中国君主往往随心所欲,大行“赏赐”。这自然会吸引更多的外邦人士前来。出于前车之鉴,明成祖朱棣自然对日本充满戒心,规定日本10年“人贡”一次,并限制每次人员200名,“贡船”二艘。醉心于中国财物的日本国人自然不满于“十年一贡”的强行限制,他们结伙而来,进入明朝境内,遇到官兵洁问,就以“人贡使者”应对。每当碰到这种“贡不如期”的情况,各级官员往往“俯顺夷情”,以“下不为例”不了了之。但这些“人贡使者”每每趁明朝守军不备之时,大肆杀掠居民,满载而归。
在这些伪装的“人贡使者”之外,为数众多的日本海盗直接用武力向明朝沿海地区进行杀掠,为此,明朝政府进行了积极的抵御,给肆虐的倭寇以沉重的打击。当时最辉煌的战役即刘江指挥的辽东望海祸之战,生擒数百,斩首千余,使来犯的倭寇无一逃脱。这一胜利力挫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倭寇不敢再组织较大规模的武装入侵。可以说,到永乐年间,随着中日关系的密切,“倭患”问题也变得日趋复杂。
正统、弘治年问,沿海倭寇入侵屡禁不止。为此,明英宗特下诏沿海地区全力备倭,遣重兵防守要地,增筑城堡,严把关口,派兵分番驻屯海边咽喉之地。严阵以待的明朝海防大大减少了倭寇偷袭的机会,使附近居民得到较大的安全感。可以说,从明初到弘治时期,沿海“倭患”问题的性质较为单纯,中日两国的关系在表面上还维持着“朝贡”往来,即使在朱元漳与日本绝交之时,沿海3个市舶司并没有废止,也就是说中日仍然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贸易关系。然而,及至世宗嘉靖年问,中日贸易关系及“倭患”问题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15世纪末,日本诸岛又陷入诸侯割据的混乱之中,各大封建主都力争向中国的所谓“人贡”权,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嘉靖二年(1523年)五月,日本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僧宗设,右京兆大夫高贡遣瑞佐及宋素卿先后至宁波。按规定,人贡须按先后顺序,由市舶司验货及招待。宗设早到一步,照例应先予接待。可是宋素卿是一位迁居日本的宁波人,熟悉明朝官场交接之道,他通过贿赂主管太监,让后者先行查验货物,而且款待规格远在宗设之上。宗设大为不满,凭借其人多势众,咆哮公堂,追杀瑞佐及其随从,并向明朝守军发起攻击。他们大肆掳掠宁波及周围地区,如人无人之境,备倭都指挥刘锦等人惨遭杀害。这一事件一时震动了朝野上下。
一小股入贡使竟然造成如此巨大的危害,这显然与明代中期海防力量废弛有着直接的联系。据记载,时至嘉靖年间,由朱元漳及朱棣等苦心经营的海防工事废坏已相当严重,战船。哨船“十不存一”,备倭卫所的士兵数量锐减,仅为原来的4/1O,这使得明朝军队在气焰嚣张的倭寇面前柬手无策。当时,内阁首辅夏言等人闭口不谈海防问题,而将这件倭人侵扰事件简单归咎于市舶司的存在,认为“倭患起于市舶”,建议罢置中舶司。明世宗以为言之有理,遂于当年罢省沿海市舶司。这一,举措可以说是明朝海禁政策最极端的表现。事实证明,这种极端的海禁政策是导致明朝中叶沿海“倭患”日益严重的最主要原因。